【自动化科技与古籍整理】
1:近年来,古籍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建设不断推进。这些兼具古籍智能化图像识别、句读标点、命名实体识别、数字化检索等功能的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自动化科技与古典文献结合起来,促进了古籍资源在智能信息环境下的深度开发、利用与传播。四川大学中国文化全球传播大数据中心教授王兆鹏提出了古籍智能化的两个面向。一是古籍文本转化智能化,二是古籍利用智慧化。
2: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我国已有多个古籍整理自动化和可视化平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在会上展示了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的样式和使用方法。
3: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晓虹看来,作为传统史料的古旧地图,因其表达方式的复杂性、精度的不确定性、收藏机构的分散性,在利用上存在较大困难。因此,需要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整合,建立共享平台以打破数据孤岛现状,提升古旧地图资料利用效率与资料检索效率。
4: 约翰·莫弗特(John P. C. Moffett),本科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汉语,并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自1992年9月以来,莫弗特一直担任英国李约瑟研究所(NRI)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与此同时,他曾在英国多个专业委员会担任职务,其中1992—2016年任剑桥大学图书馆自动化集团(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utomation Group)执委会委员等。
李约瑟研究所的汉籍守护与学术传承

莫弗特在李所门前,身旁是李约瑟雕像。 资料图片
约翰·莫弗特(John P. C. Moffett),本科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曾于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汉语,并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自1992年9月以来,莫弗特一直担任英国李约瑟研究所(NRI)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与此同时,他曾在英国多个专业委员会担任职务,其中1992—2016年任剑桥大学图书馆自动化集团(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utomation Group)执委会委员,2004—2008年任国家东方图书馆资源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Oriental Library Resources)执委会委员,2001—2004年、2006—2008年两度任伦敦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执委会委员等,并与他人联合主编了《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中西书局,2020)等。
2021年11月20日,CCTV科教频道开始陆续播出纪录片《李约瑟和中国古代科技》。该片分为《到中国去》《先生之风》《文明高地》《神奇创造》《书写中国》《人去留影》六集,讲述了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的奇特经历。片中,我们看见一位高挑帅气的老外在作解说;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满怀深情地向观众讲述李约瑟博士在战时中国拍摄的图片、所写的个人笔记及其他资料,引导观众一道探讨李约瑟与中国的相识相知,展示《中国科学技术史》(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项目的前因后果。他,就是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约翰·莫弗特。

李约瑟研究所落成纪念牌匾 作者/供图
笔者曾于2020年3月短期访学于李约瑟研究所,并就该所的发展历史与汉籍域外的守护与传承等话题访谈过莫弗特先生,近期又通过电子邮件作了补充采访。让我们随着莫弗特的讲述,来深入了解一下李约瑟研究所以及他本人在中英文化交流中的往事秘辛与独特贡献。
求学爱丁堡 留学北京城
孙继成: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教育背景。
莫弗特:我于1982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大三时被学校派往北京语言学院留学一年;本科毕业后,在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赞助下,我又申请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两年。1984年夏天,我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从事图书编辑和翻译工作。
孙继成:当年爱丁堡大学的老师有怎样的汉学传承?
莫弗特:当年给我上汉语课的老师共有四位。秦乃瑞(John Derry Chinnery, 1924—2010)教授当时教过我们语法和现代汉语,他是一位有名的鲁迅研究专家。1965年,他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调到爱丁堡大学,创办了中文系,并担任系主任和汉学教授;他的太太是BBC记者陈小滢,是中国著名作家陈源(陈西滢)的女儿。早年秦乃瑞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汉语时,曾做过萧乾的学生。1954年他曾带团访问中国,还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1966年,他与李约瑟、韩素音(Elisabeth Comber,1917—2012)一起创立了苏格兰—中国协会(Scottish-China Association),促进中英文化的交流。而文言文课程是由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老师授课。斯科特老师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他教我们读古汉语(唐诗等)。还有一位华人老师,叫窦道明(Francis Dow),他教我们口语。杜为廉(William Dolby, 1936—2015)老师也教我们古汉语(《三字经》《老子》《韩非子》、明清小说、元杂剧、诸宫调等)。杜老师本科就读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师从刘若愚(James Liu,1926—1986)、白芝(Cyril Birch,1925— )、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等著名汉学家,常年从事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从大二开始,老师们就不再在课堂上教授单词了,开始让我们自己去学着使用词典,自己查生字难词。整体说来,我们当年学习文言文的时间较多。
孙继成:请您回忆一下在中国的留学生活。
莫弗特:1980年9月,我去中国留学。除了爱丁堡大学,当年英国政府派往中国的留学生,还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利兹大学、杜伦大学等校。当时老师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想学好汉语,最好还是去中国学。在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后,我的汉语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还是不满足,于是在大学毕业后的1982年,又向英国文化委员会申请到了一笔奖学金,这样我就来到了北京大学。其实,当时北大中文系对外国本科生的访学深造,并没有制定出相应的课程培养计划,既没有给我指定导师,也没有考试要求,所以,我听课就比较自由随性。我听的课程不算太多,主要是选听了与明清小说相关的一些课程。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图书馆看书,或者待在勺园的宿舍里看书。
孙继成:回国后,您就到李约瑟研究所工作了吗?
莫弗特:不是的。1986年4月初,我返回英国,就去了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定下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左传》的研究,导师是杜为廉老师。但博士论文还没有写完,我就在1992年9月来到了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工作。由于所里的工作十分繁忙,后来我就没有继续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为研究东亚科技及医学史的学者们服务好,为他们来研究所学习研究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和宝贵的文献资料,而这也是我们研究所的学术使命之所在。
援建研究所 助编科技史
孙继成:请您谈谈初到研究所工作时的情况。
莫弗特: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之后,每天下午我都能看到李约瑟博士坐着轮椅来所里上班。他会准时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忙着《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可以说是风雨无阻,很有规律。到了晚年,研究所便为李约瑟聘请了几位私人科研助手,当时就是一位名叫孙蕾馨(Tracey Sinclair)的协助李约瑟处理日常信件往来、查找资料等。
当时还有我们的前任图书馆馆员希拉里·程(Hilary Chung)女士。她的先生是从越南移民来剑桥的华裔。后来她拿到了博士学位,就去了别处工作。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的前期工作主要都是由她来完成的。还有第二任所长何丙郁(Ho Peng-Yoke,1926—2014)教授和一位兼职秘书安哥拉·金(Angela King),但我是研究所里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也是唯一的带薪职员。
孙继成:李约瑟研究所采用的是怎样的运作模式?
莫弗特:李约瑟研究所是一家独立的慈善研究机构。本所与剑桥大学没有任何财务关联,接受李约瑟基金会董事会的直接领导,由基金会主席负责所务安排,由基金会财务主管负责所有财务往来。
研究所创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的研究和发展,进而推进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了解和融合。研究所基金会董事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所长选聘,并委托所长负责研究所的管理和运行,但需要所长每年向董事会进行数次情况汇报。由于研究所在财务上独立于大学,也没有政府拨款资助,所以,所长的最大职责就是为了研究所的顺利运营而到处筹款,争取社会各界的捐助。
孙继成:李约瑟早年都有哪些助手和项目合作人?
莫弗特:根据研究所的史料记载,李约瑟早年的科研助手有王铃(1917—1994)、鲁桂珍(Lu Gwei-djen,1904—1991)、黄兴宗(Huang Hsing-tsung,1920— )和曹天钦(1920—1995)等,负责协调《中国科学技术史》项目的整体推进。李约瑟最早的助手是王铃,他是李约瑟当年在战时中国就已结识的历史学者,当时就职于重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受所长傅斯年的委托派遣,于1947年来到剑桥,协助李约瑟博士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和研究。1957年,王铃在剑桥与李约瑟合作了9年之后,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了历史学教授,其助手工作由鲁桂珍接手。1956年,在李约瑟的劝说下,鲁桂珍辞去了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工作,返回剑桥做了他的助手,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另外,李约瑟还有一个长期合作人,叫罗乃诗(Kenneth G. Robinson),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部分的声学研究。
孙继成:您来图书馆工作时,正是何丙郁教授接任第二任所长的时期,当时研究所的运营情况如何?
莫弗特:根据何所长的回忆材料所记,在他接任所长职务时,李约瑟向他提议让其助手黄兴宗担任研究所的副所长,主管财务往来;建议让鲁惟一(Michael Loewe,1922— )担任业务副所长,协调《中国科学技术史》项目的推进。
由于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李约瑟后来只能专注于自己所从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估计他已无暇也无力顾及研究所未来的发展走向、职员升迁等问题。同时对于剑桥大学及东亚系提出的一些合作建议,他也有心无力,未能予以积极回应,致使研究所与剑桥大学校内的一些合作一度陷入停滞。当然,对于90多岁高龄的李约瑟博士,大家都心怀尊敬;对于其无暇他顾,也表示理解。何丙郁所长的上任,使得一些停滞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
孙继成:接任所长之前,何丙郁教授已与李约瑟博士合作多年。他也是第一位不拿薪水的所长,对研究所的存续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也为所里的筹资捐款立下了汗马功劳。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何所长的情况吗?
莫弗特:何丙郁所长早先是马来亚大学新加坡校区物理系的高级讲师,1964年调到吉隆坡校区担任中文系主任和汉学教授,从而完成了从物理学到汉学的学术转身,在工作和研究方面都表现了较强的适应能力。1953年,他做了马来亚大学副校长奥本海姆(Sir Alexander Oppenheim,1903—1997)教授的博士生,因自己的研究选题需要外审评阅而结识了李约瑟博士。他最初的博士论文选题是13世纪中国的数学文献研究,通过香港朋友黄丽松(Rayson Huang,1920—2015)的介绍,何教授才得知李约瑟博士一直在研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后来,在李约瑟的建议下,何教授的博士论文选题改为翻译与研究《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学及占星术等文献,并将它整合到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出版计划中。就这样,李约瑟博士成了何丙郁博士论文的校外指导老师。何教授于1954年博士毕业,1957年11月从马来亚大学争取到了八个月的带薪学术休假,来到了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进行访学,学习李约瑟的研究方法,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当年给他的学术任务主要是搜集和整理《道藏》中的化学史资料。由此,何丙郁开启了与李约瑟博士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合作。
孙继成:在您看来,何丙郁教授加入李约瑟研究所后作出了哪些独特贡献?
莫弗特:何丙郁教授具有物理学专业的理科背景和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他自身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及西方教育的历练,对于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项目也具有较强的补充作用;何教授众多的社会关系对于李约瑟研究所的筹款捐助更是意义非凡。另外,何教授还直接参与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三部分“炼丹术篇”及第七部分 “火药篇”。据记载,经过何教授的牵线搭桥,李约瑟研究所还于1984年接受了所里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是新加坡陈振传(Tan Sri Tan Chin Tuan,1908—2005)先生捐助的35万英镑,其中10万英镑用于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舍的建设,以为李约瑟收藏一生的图书提供一个安放之所。随后,他帮忙争取到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捐款用作李约瑟研究所南侧会议室的建造。1990年,接任所长之职后,何教授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并通过朋友的介绍,为李约瑟研究所争取到了每年1万英镑的项目捐助,用来购买大量的汉语图书。美国纽约基金会的捐款则用来资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图书出版和购买英文相关研究文献。
孙继成:据您观察,何丙郁教授与李约瑟在工作方法上有何异同?
莫弗特:与首任所长李约瑟一样,何丙郁所长也是理科出身,后来才转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他独特的学术经历和地位,以及与众不同的教育背景,使他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眼光、处事智慧和个人魄力,也使他能够自由穿梭于欧亚澳美四大洲,进而在跨领域、跨文化、跨学术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令人欣慰的是,何丙郁教授担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之职长达12年,为研究所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东亚筹善款 所长谋发展
孙继成:有关资料显示,1979年至1986年期间,李约瑟博士本人为了研究所的发展而去东亚进行筹款演讲,以争取社会各界的捐助,但这却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项目的写作进度。
莫弗特:是的,这次东亚之行,路途遥远、鞍马劳顿,对于这么高龄的老人来讲,确实不易。但李约瑟的这次东亚筹款演讲,也推进了学界对东亚科技史研究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医药史研究渐成新的学术动向。有了资金保证,研究所才能正常运转,我们才能进一步完善书籍的馆藏。我到李约瑟研究所工作之后,曾委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代为购书,及时补充了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相关书籍,弥补了多年来没有购买新书的缺憾。为了满足研究中医学史的几位英国博士生的论文需求,我还为他们采购了最新出版的医学史文献,同时也丰富了研究所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越来越专业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来此进行学术交流;国际学术界也开始从社会、政治、宗教、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乃至东亚的科技史和医药史。
孙继成: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状况,李约瑟研究所曾经协助拍摄过一部名为《龙腾》(The Dragon’s Ascent Project)的纪录片。它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莫弗特:《龙腾》是由李约瑟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英国独立制片人麦启安(Francis Gerard)、阿利斯泰尔·米基(Alistair Michie)联合制作,历时四年(1998—2002)才得以完成的纪录片。该片以中国从古至今的科技文明发展为主题和主线,分八集讲述了中国的治(History as a Mirror)、家(Family Values)、术(Forging the Future)、农(Feast or Famine)、医(The Health Culture)、天(Power to Predict)、迹(Two-way Traffic)和飞(The Dragon Ascends)。据说,这部总时长为八小时的《龙腾》纪录片,成了西方媒介史上时间最长的中国主题纪录片。《龙腾》播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为李约瑟研究所带来了丰厚的资金回报,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探索,同时也为李约瑟研究所的稳健发展奠定了财政基础。
孙继成:据说贵所第三任所长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1946— )教授是首位带薪所长,他是何时开始与李约瑟博士进行学术合作的?其学术研究有何特点?
莫弗特:古克礼教授是国际知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本科和硕士就读于牛津大学工程系。在获得工程科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师从刘殿爵(D. C. Lau,1921—2010)教授研习中国古典文献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早年,他做过中学物理教师,后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担任科技史讲师,研究兴趣广泛,涉及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医学及工程技术等领域,是一位成功的跨界学者。
何丙郁教授担任所长时,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任教的古克礼就兼职做了常务副所长,每周五会从伦敦赶来剑桥上班一天。从1992年起,他就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著作的出版工作,2003年接任所长职务之后,他致力于完善李约瑟研究所这一学术平台,并团结东亚各国学者进行东亚科学技术、医药史等的编撰协作。
李约瑟博士让世界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古代科学与技术,而古克礼教授则致力于人类普遍性的研究。他认为,科学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东西,科学研究是一种边界模糊的大型社会活动,也是理性理解世界的一个过程;在研究人类普遍性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交流与融合,发现并欣赏不同人群所展现的文化多样性;通过了解别人的不同,来加强对自我的理解,进而求同存异,使得世间安好。
2013年3月20日,经过全球招聘,致力于研究古代金属技术史的中国学者梅建军教授当选为第四任所长。梅教授的成功当选,标志着李约瑟研究所在国际东亚科学和文化研究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并将为剑桥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作出积极贡献。在梅教授的努力下,研究所增添了新的科研资助项目,为国际科技史、医药史研究学者提供了更好的科研条件。
编汉籍善本 守护且传承
孙继成:当年李约瑟的个人藏书量到底有多大的规模?
莫弗特:大约有1万册汉语图书,2万册其他语言的图书,另有2万册复印本和60种杂志。
孙继成:数量确实惊人。我们知道,在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李约瑟生前从东亚搜集的汉文古籍。2020年,您与陈正宏教授主编的《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得以出版,请谈谈该书的图目情况。
莫弗特: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近60年中,李约瑟博士搜集了近700部汉籍。虽然这些典籍并非珍稀善本,但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和医学史的研究却至关重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陈正宏教授与我们合作,就该书的整理与编目问题做了多次探讨;后来,他三次来访剑桥,才最终完成了《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这部书的编纂工作。该书的书目共选择善本100种,依据汉籍善本书目著录规范,对每一种都进行了著录,其中包含了完整的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版式行款、藏书印鉴,同时配有古籍彩色书影。对于所有中文条目和注释、图示等,我都择要译成了英文,以供学者参考。在图目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大量国际友人的帮助和支持。图目的出版,使得李约瑟博士收集的珍贵汉籍向世界作了集中展示,也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新的文献入口。
孙继成:18世纪以来,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汉籍文献数量众多,是汉文世界的宝贵财富。尤其是汉学家及汉学研究机构所收藏的中国古籍,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近年来,随着国家重点项目“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深入开展,“域外汉籍”的鉴定和编目等建设逐步深入。对此,您有何评论?
莫弗特:在域外汉籍图书收藏与编目整理等方面,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早期主要是整理李约瑟个人的汉籍收藏,并进行图书编目,后期才逐步转为补充采购最新出版的东亚科技、医药史文献。在四任所长的共同努力下,李约瑟研究所有关中国及东亚科技史文献的收藏已渐具规模,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孙继成:请问英国还有哪些图书馆设有汉学文献专藏区?
莫弗特:在英国高校中,设有汉语文献专藏区的大学图书馆曾成立了一个组织,名曰中国图书馆联盟(China Library Group,莫弗特为现任主席)。它的主要成员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利兹大学、杜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该联盟就各校馆藏的汉语图书购买、编目格式、数字化共享、馆际合作、国际交流等进行深入交流,为英国的汉学发展提供了文献支持。

李约瑟研究所研究人员学术分享会(2020年3月6日) 作者/供图
搭桥又铺路 专业平台秀
孙继成:好多学者都是利用自己的学术假期来李约瑟研究所做调研,从开具邀请信到剑桥的学习生活,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您的细心协助。请问贵所接受学者来访的遴选标准是什么?贵所对来访学者及其研究有何要求?
莫弗特: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到访李约瑟研究所,他们中有研究亚洲科技史的西方学者,也有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的东方学者。访学时间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一到三个月。只要他们的研究与李约瑟研究所的馆藏文献相关,我们都欢迎他们来访,并为其科研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另外,李约瑟研究所还根据自己的科研项目规划,面向全球招聘相关学者,并提供一定的科研资助。来访学者在此都可进行独立研究,我们一般会安排学者就自己的研究内容进行一次或数次讲座,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研究与发现。访问学者还可参加李约瑟研究所的每周文本研讨会,一起研讨如何解读典籍的原文。
李约瑟研究所与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不同,研究所本身并不开设特别课程,也不提供论文的写作指导。本所与剑桥大学本身的多学科协作的传统,保证了来访学者每周都能出席不同领域的研讨会,有机会拓展和更新自己的知识谱系。
孙继成: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我们看到了马可·波罗、利玛窦、李约瑟等国际友人的披荆斩棘和艰难前行。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李约瑟及其研究所的同仁们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更多国际友人携手共创、搭桥铺路,为世界文明互学互鉴、共同发展而继续努力。最后,请您展望一下研究所发展的愿景。
莫弗特:目前,在第四任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领导下,李约瑟研究所发展势头良好。近年来,来所里访学的国际学者越来越多。这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尽管各地来访学者无法亲临所里查阅图书,但我们充分利用网络会议的便利,保持研究所定期举办专题研讨会的传统,团结所里来访过的“李友”。希望疫情散去,放开国际旅行限制,大家又可重聚在李所,探讨世界科技史、医药史的奥秘。
中国历史上涌现出来的“钱学森之问”“李约瑟难题”等,时刻都在提醒我们:不同文化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比较,而文化比较可以促进多种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李约瑟研究所的发展史,希望研究所能够成为国际学者探究全球科技史、医药史的学术平台,为不同文明的深入交流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作者系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MTI校外合作导师、山东理工大学翻译系副教授)
新技术为古籍整理注入活力
3月12日,“古籍智能信息处理”系列研讨会第一讲“智能时代古典文献学的机遇与挑战”在线举行,与会学者围绕“智能信息环境下古典文献领域应用的技术、工具和平台”等议题展开交流,共同展望古籍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与前景。
拓展文献整理与研究新方向
古籍传承和保护历来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古籍智能化、信息化为古籍整理与研究提供了良好发展机遇。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认为,智能技术使古籍整理的对象、重点发生改变。过去,古籍整理的目标是把传统纸本古籍整理出来再次出版,或者以现代文的注释便利大众阅读。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将古籍文献中所蕴藏的古代历史文化知识抽取出来,构造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库,以知识图谱的形式支持互联网前端应用。另外,在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支撑下,古典文献学和相关领域的跨界融合越来越明显。
在智能信息环境下,古籍整理和古典文献的研究与教学正面临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峥认为,凝聚社会多方力量,推动古籍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建设,形成相关标准规范,是古典文献学在智能时代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古籍整理和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根本改变,即用新技术、新流程、新视角来整理古籍、解析文本。
大数据技术促进了传统文献学的现代转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石认为,传统的文献研究主要以细读经典文本的方法来研究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经典文献。在全文数据库时代,这些文本只能算是样本,不能概括或代表历史全貌。大数据技术追求的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部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大数据技术的使用,有望在研究的科学性、整体性与理论范式上,促进传统文献学的现代化转型。
推进数据平台建设与资源共享
近年来,古籍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建设不断推进。这些兼具古籍智能化图像识别、句读标点、命名实体识别、数字化检索等功能的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古典文献结合起来,促进了古籍资源在智能信息环境下的深度开发、利用与传播。四川大学中国文化全球传播大数据中心教授王兆鹏提出了古籍智能化的两个面向。一是古籍文本转化智能化,二是古籍利用智慧化。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我国已有多个古籍整理自动化和可视化平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在会上展示了浙江大学“智慧古籍平台”的样式和使用方法。他表示,传统古籍整理方式主要是个体作业,以书为单位,由人力完成,不能修改、不可关联。而大数据时代的古籍整理方式是众包作业,以篇目为单位,通过人际合作共同完成,可随时修改和关联。这就是传统古籍整理与大数据背景下古籍整理的最大不同。
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晓虹看来,作为传统史料的古旧地图,因其表达方式的复杂性、精度的不确定性、收藏机构的分散性,在利用上存在较大困难。因此,需要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进行整合,建立共享平台以打破数据孤岛现状,提升古旧地图资料利用效率与资料检索效率。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古籍文献数据化的推进,作为传统史料的地图也受益于GIS技术,古地图的研究从单纯的古旧舆图编目整理,逐渐向数据平台建设与资源共享转变。
正视新技术局限性
大数据技术在古典文献研究中也存在局限性。刘石认为,“用数据说话”不等同于“数据即是客观事实”。数据量大,并非意味着有用的信息多。
信息智能技术与中国古典文献的结合,是一个有着深厚发展潜力的交叉学科领域。王军表示,在这种形势下,高校古典文献学专业如何培养兼具技术与学术能力的古典文献学人才,如何形成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信息化时代,人们仍然需要加强古籍阅读,以提升人文素养,同时也要倡导跨学科、跨环境、跨文化、跨地区合作。
杨海峥提出,在教学和人才培养层面,要丰富、调整原有教学内容,增加新内容,更新教学理念、方法、手段。在研究层面,要利用好现有的平台和技术,根据学者个性化需求开发新技术,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合作,以新技术解决新问题。在古籍整理层面,人文社科学者要与技术人员合作,保证结果的准确性,确保更好地“利用”机器而不是被机器“误导”。
在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院教授金连文看来,古籍图像增强、修复,复杂版式古籍文档图像版面分析等问题尚待解决。未来,要推进古典文献学、文字学研究者与AI学者密切合作,使文献学研究与先进技术充分融合,协作推动古典文献学繁荣发展。
会议由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共同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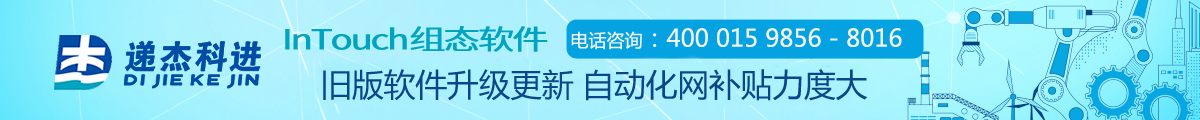

评论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