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好高质量发展人文观察与学习:推恩】蒋国保教授文中指出:
- 孟子认为:对于人来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不得于亲,不可为仁”(《孟子·离娄上》),“仁爱”精神的实质,并非根本体现在人对其他动物之痛苦的不忍心,而是根本体现在人对自己父母之血亲情感。所以,“仁术”云云,就是指人将其侍奉父母所体悟出来的“爱”的情感推广开来的办法。对这个办法,孟子特意创造了一个范畴,称它为“推恩”。
- “推恩”说在孟子思想中,与其说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治人方术论,不如说是纯哲学意义上的“做人”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态的“做人”论,“推恩”说在理论上有几大理念支撑。
- 在《孟子》中,“推恩”仅二见,均见于《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作者简介丨蒋国保,安徽大学方以智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文载丨《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责任编辑:张利明

摘要:
孟子“推恩”说,上承孔子“忠恕”说,下开理学家“万物一体之仁”说,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明。“推恩”乃儒家“仁爱”之术,是指人藉推己及人的方法将人之血亲情感普遍地诉诸他人。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以及基督教“博爱”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的“兼爱”,计较在交相利,基督教的“博爱”考量在契约回报;提倡契约上的平等回报,其实也就是在提倡利益计较,则较之墨家“兼爱”及基督教“博爱”,儒家“仁爱”显然具有非“功利”性、非“契约”性之特色。就精神文明形而上而物质文明形而下来说,儒家“仁爱”因倡导无“功利”计较的泛爱众,在精神境界上要比重“功利”考量的“兼爱”及“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
关键词:儒家;孟子;推恩;仁爱;兼爱;博爱;
文化与文明之所以相通,就在于它们都是人之创造的产物。但相通不等于相同。文明不同于文化,就在于文化是对人之创造物的统称,而文明则只是对人之创造物的特称。人之一切创造产物,不论其良劣如何、先进还是落后,都统统归在文化名下;文明则不然,它作为人之正能量创造的产物,仅用来称谓那些代表人类文化进步的人的创造物。文明是对文化的价值贞定:是文化的,未必是文明的;是文明的,则一定是文化的。文明是先进文化的价值显现,它在本质上不属于落后文化。由此不难推断,作文化比较,务必要分析不同文化所反映的不同的创造力当归于什么样的生命精神类型,却不必非得去分析不同文化在价值上的优劣高低;而作文明比较则不然,它可以不分析不同文明所代表的文化类型有何差异①1,但决不能不分析不同文化在价值上有何优劣高低之不同。本文不是从文化类型说的层面探讨儒家“推恩”说的理论特征,而是从文化价值说的层面探讨儒家“推恩”说的实践价值与意义,所以本文立论不着眼于“儒家文化”而着眼于“儒家文明”。
一、孟子“推恩”说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儒学即人学,旨在揭示人之存在本质。儒学认为,人之最根本的本质即“爱人”。可如何实现人之“爱人”本质?孔子的回答,有些含糊,而孟子却明确地回答说:它靠“仁术”来实现。在孟子看来,儒家的“爱人”关切,只有通过“仁术”才能具体落实,实现其实践意义。那么,“仁术”何义?“仁术”在《孟子》中仅一见,即见于《梁惠王上》第七章,系孟子解释梁惠王(魏惠王)“以羊易牛”之行为合乎人性所用语。梁惠王看见将杀之以“衅钟”的牛之“觳觫”而不忍心,让放了牛,易羊以“衅钟”,这被百姓误解,以为他“以小易大”乃出于爱财,而孟子认为这正是梁惠王行“仁术”的表现:“无伤也,此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2由此可以看出,孟子所谓“仁术”,具体是指人将自己不忍心看动物痛苦的情感付诸免除动物痛苦之行动的操作手段,但实际上“仁术”在孟子那里决不只是作为人关爱其他动物之特殊手段来看待,他更将它视为人能落实“爱人”精神普遍有效的办法。孟子认为:对于人来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不得于亲,不可为仁”(《孟子·离娄上》),“仁爱”精神的实质,并非根本体现在人对其他动物之痛苦的不忍心,而是根本体现在人对自己父母之血亲情感。所以,“仁术”云云,就是指人将其侍奉父母所体悟出来的“爱”的情感推广开来的办法。对这个办法,孟子特意创造了一个范畴,称它为“推恩”。
在《孟子》中,“推恩”仅二见,均见于《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3可以看出,“推恩”虽然是孟子作为政治统治术向梁惠王提出的,但孟子对什么是“推恩”以及如何“推恩”的论述,却体现了他关于人何以“善推其所为”的哲学思维:人若善于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推广的话,就会“举斯心加诸彼”,用自己对待家人的情感对待别人,敬重自家的长辈,就推己及人也尊敬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家的儿女,就推己及人也爱护别人家的儿女。
由此可见,“推恩”说在孟子思想中,与其说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治人方术论,不如说是纯哲学意义上的“做人”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态的“做人”论,“推恩”说在理论上有几大理念支撑。
首先,就本体论来说,孟子认为人能“推恩”取决于“人”之先天的实践理性或曰道德实践能力。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也几希”(《孟子·离娄下》),认为人与禽兽相区别之处极少,或者说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就那么一小处。那么,足以显示人之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那小小的一处是什么?它就是指唯有人才具有的而其他动物不具有的“由仁义行”(《孟子·离娄下》),或者说“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的能力。“由仁义行”是按“仁义”行动的意思。按“仁义”行动,亦即顺从“仁义”做人,实现人之存在意义上的内在道德认同与外在道德实践的高度统一。按照孟子对“仁义”的区分,即“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人的行为分内外,一方面以“仁”安顿人之内在的心灵,另一方面以“义”规范人之外在的行动。“仁”安顿于人心,“人心”就自然成为“仁心”;“仁心”立,则“义”起,人对自己行为之正当性与否,就会本然的觉悟,就会循正路行动。孟子认为由这种本然的觉悟所开之心境,亦即无私无欲的清明心境,它使得“仁义之心”得以保存;反之,清明心境一旦丧失,“仁义之心”也就随之丢失。为了不使“仁义之心”丢失,就必须“养心”,而“养心莫如寡欲”(《孟子·尽心下》),保养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减少欲望,因为唯有不断减少私欲才能达到心境的清明。由清明心境确立起来、保存下去的“仁义之心”,亦即人的“良心”,它见诸对象,谓之“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它“不学而能”(《孟子·尽心上》),谓之“良能”;它“不虑而知”(《孟子·尽心上》),谓之“良知”。“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云云,无非是强调人的“良心”的发用,非根源于一切后天的因果性,而是先验的。由“不忍人”“良知”“良能”构成本质的人之“良心”,是人所“皆有”,是人所“心之同然”,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乃道德存在,先天的具有道德理性。所以,任何人,只要扩充自己的“良心”,都会成为有道德的人,即外在行为上顺乎道德理性的人。
由上面的论述来看,孟子反对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张“仁义由内”4,并不是旨在否认人之行为有内外之分,更不是旨在否认人之内外行为有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而是将仁义都作为人之先天的道德律令——“仁”是指发端于“恻隐之心”的道德贞定,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义”是指发端于“羞恶之心”的道德贞定,即“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藉以将人之一切道德规范统摄于“仁”,以便以“仁”归纳人之存在本质,即“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以“仁”规定人之存在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仁”才是做人的根本原则,所以孟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孟子·离娄上》),强调如何做人只有“仁”与“不仁”这两条做人原则可以选择。原本只有一个原则,若从正负两面把握,就成了仁与不仁。人之善恶,取决于人是否选择“仁”这一做人的原则以做人。
其次,就人性论来说,孟子认为人之能“推恩”取决于人之本性善良。孟子“道性善”(《孟子·滕文公上》),认为人具有善良的本性。可人之本性何以善良?这个问题,以战国中期之三种人性说——“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孟子·告子上》)——来解,都无法得出合理的解释。孟子于是转换致思取向,“即心言性”5,以人的“本心”为善来证明人之“本性”为善。“性善”即“心善”,在孟子的论证中,被规定为人之道德性扎根于人心:“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心”分“小体”与“大体”,小体之心,指作为思维器官的心;大体之心,指作为道德理性的心。小体之心的发用,是人自然具备的能力,无所谓善不善;而大体之心的发用,却必定基于道德6。由此可见,“心善”即“性善”,在孟子的论述中,被规定为人之道德本心的发用从意念萌动起就自然地合乎道德。正因为人的本心就是“性”上即“善”(合乎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心——良心,所以人之“良心”不发便罢,它一旦发用,人就会出于善心而无法漠视别人痛苦与不幸,从而一定生同情心、怜悯心。这种同情心、怜悯心是“推恩”得以完成的先决条件,因为人若无同情、怜悯的情感,对别人的不幸与痛苦甚至悲惨熟视无睹,人又怎么能以“仁术”处理人际关系,将血亲之爱的情感推广开来,扩充为爱他人的普遍情感。
再次,就人格论来说,孟子认为人之能“推恩”取决于人之人格上的平等。孟子承认“人格”的多样性。在他看来,同是人,由职业分,有矢人、函人、虞人、校人之别;由道德分,有端人、善人、信人、妄人、恶人之殊;同是男人,由性格分,有顽夫、懦夫、薄夫、鄙夫之差;同是庶人,由居处不同,在政治地位分为“市井之臣”与“草莽之臣”;同是士,由道德高低,分为大人、小人;由地位高低,分为元士、下士、中士、上士;同是圣人,但各有特性:“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但是,孟子并不因承认人格的多样性而否认人人都有相同的类本质——异于禽兽,乃道德存在。人与人的不同,只能视为“放心”与不“放心”之别,不能看作德性才质上的差异。本然的不“放心”为圣人,是普通人绝对做不到的。对普通庶民来说,时时“放心”却是生命常态。但“放心”并不意味着人彻底丧失了自己之本心——良心,只是意味着本心——良心之暂时游离于人的生活。人为了保证自己的本心——良心不至于彻底丧失,固然要通过“寡欲”来“养心”,使本心——良心不至于因膨胀的私欲之遮蔽而丢失;更重要的是,在本心——良心丢失时,要自觉“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使那游离状态的本心——良心返归其本然状态7。人心之本心——良心状态,亦即人所固有的“仁心”状态,它“不学而能”,谓之“良能”;它“不虑而知”,谓之“良知”。由“不忍人”“良知”“良能”作为本质构成的人之本心——“良心”,是人所“皆有”的,是人所“同然”。既然人人皆有本心——良心,那么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能扩充其“良心”,推恶恶之心、好好之心,就能成就理想人格,由普通人成为圣人。孟子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孟子这样强调,当然并非武断地断言人必定都能、真能成为圣人,而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人格理念:人因为先天具有相同的本心——良心而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孟子说:“钧是人”(《孟子·告子上》),又强调说:“舜人也,我亦人也”(《孟子·离娄下》),将其人格平等的理念表达得十分明确且清晰。人之人格上的平等,从根本上保证了人之“推恩”的可能,因为要“推恩”人就得因自己是个人而把别人当人待;如果人在人格上不平等,那么人基于其人格不平等信念,人又怎么能做到把人当人待;若人不把人当人待,人又如何能“推恩”,用爱己爱亲朋的情感去爱陌生人。
最后,就人才论来说,孟子认为人能“推恩”取决于人有充类的才能。孟子强调人乃道德存在,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无本质上的高低、贵贱之分,但亦指出:就自然人而论,人的才能毕竟有大有小,不可能在能力上完全相等。人之知识理性意义上的能力不等,在孟子看来,并不是指有的人有知识理性8 ,有的人不具有知识理性,而是指圣贤与普通人在知识理性——充类能力——上的差别:圣贤能够出于“本心”而自觉地扩充“良知”“良能”,将“良知”“良能”的呈现对象化,即体现为“爱人”;庶民却不能直接地本诸“本心”呈现“良知”,有必要通过“推恩”完成“良知”“良能”的呈现,实现内在“良心”之客观化、对象化,即变成同情人、怜悯人的爱心。孟子将人这样完成的“本心”——“良心”的客观化、对象化,就方法上称为“推好‘好’之心”,“推恶‘恶’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推者,推及也,类推也。由“推”字作此意用可推断,在孟子看来,人之固有的能力“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孟子·梁惠王上》),人一旦善于推其所为,将自己喜欢好事好现象而讨厌坏事坏现象的情感类推开来,人就能将自己内在的本心(良心)扩充为外在的爱人之心。这就是“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孟子·尽心下》)
二、“推恩”说的思想源头及其精神延伸
儒学是仁学。“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学对人的本质的揭示,重在将人之所以能“群”(组成社会)、所以有“德”、所以能“乐”归结为人在本质上能“爱人”。儒学范畴里的“爱人”,其所谓“爱”特指“仁爱”。“仁爱”所讲的人之爱,不是指个体的一己之爱,而是指个人对他人的爱。就独立的个体而言,人之爱亲人与爱陌生人,都属于爱他人。但儒学强调,这两种爱的情感呈现方式是不同的,爱亲人是人将血缘亲情直接地流露、表达出来;爱陌生人则是人将自己爱亲人的爱心扩充出去。这两种爱,本质上都体现了人之善良本性,程度上有爱亲人与爱陌生人所付出的情感不等。既然爱之情感付出有直接与间接之表达方式之别,亦有大小程度之别,那么,人之由血缘亲情之爱如何扩充转化为对朋友乃至陌生人之爱?这用孟子的术语来回答,就要通过“仁术”来实现,亦即如上文所论,要靠“推恩”实现。
但必须强调的是,在儒学史上,“推恩”一词固然由孟子首先提出并使用,但其思想源头就是孔子“仁学”所强调与提倡的“仁之方”(《论语·雍也》)。“仁之方”,是人之个体“能近取譬”(《论语·雍也》)的方法。作为关系中的个体,最贴近人者就是人自身,所以“能近取譬”就是人就自己打比方的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推己及人”方法。“推己及人”的方法,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将它明确规定为“忠恕之道”。9“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与“推恩”作为“仁术”,在精神上高度吻合,两者在思想上存在源与流的密切关系,是毫无疑问的。
儒家“仁学”为孔子所创立。“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创立“仁学”,旨在倡导“爱人”。然而孔子又认为血缘亲情更为重要,强调人当“爱人”决不能被引向“爱路人胜于爱亲人”10之歧途。“爱路人”与“爱亲人”,固然都属于“爱人”,但在孔子看来,“爱有差等”,两者在爱之情感付出程度与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别:爱亲人的情感浓烈、方式直接;爱路人的情感平淡、方式间接。一方面坚持“爱有差等”,要求“爱亲人胜于爱路人”;另一方面强调献爱心,要求普遍地爱别人,两者岂不矛盾冲突?孔子认为并不矛盾冲突。何以见得?孔子这样回答:虽然应据实承认“爱有差等”,但也要明白爱有差等并不足以否定普遍爱心之存在及其意义,因为完全有可能由对亲人的偏爱走向对别人的普遍关爱11。可能的即合理的。之所以合理,是因为人之为人从本质上讲可以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儒家以“忠恕之道”作为“仁之方”,正是要告诉人们,从亲情之爱可以合理地推及普遍爱心。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将“忠恕之道”具体作两方面规定,一是将“忠”规定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二是将“恕”规定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所谓“忠”,就是要求尽力地帮助别人,是付出爱心的主体对自己的积极诉求;所谓“恕”,就是不要将自己所不愿干的事强加给别人,是付出爱心的主体对自己消极的约束。就个体美德讲,为了实现“爱人”的价值,“忠”和“恕”都是必要的,但作为社会交往的规范伦理,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做到尽力地帮助别人,却必须要求每个人按“恕”道行事,决不可将自己的“不欲”强加给别人。这应该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失去了这个准则,人类除非不交往,若交往的话,那么只能遵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将自己混同于禽兽。
孟子对儒家仁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将孔子的“仁之方”简称为“仁术”,并以“推恩”来界定“仁术”之兼有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更在于其“推恩”学说在思想上开启了后孟子时代之仁学发展历程,成为汉唐宋明清“仁学”之直接的思想源头。为反映这一事实,下面主要举汉代与宋明的例子以扼要地叙述后孟子时代的“推恩”说。
汉代的“仁学”,以系统性言,当以董仲舒的“仁”论最值得重视。较之孔孟的“仁”论,董仲舒的“仁”论,最显著的特征是将“仁学”由“人学”改为“神学”。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12,将最高的神格规定为“天”。作为最高位格的“神”,“天”主宰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一切存在及存在样态与方式。就人而言,“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13,“天”之主宰就体现在“天”造就人及其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天”造就人,不是说人的肉体由神(天)以某物质元素或材料做成(比方说女娲以土抟成人),而是说“人副天数”14,即将人之骨节、五脏、四肢、官能,性格、情绪、思虑、道德,与“天数”作直接等同比附——“身犹天也”15,例如人“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16。基于此“天人一也”17认识,董仲舒势必以天的意志来规定人的本质,强调人以“仁”为本质是因为“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18而予人以“仁”。“天”予人以“仁”,按照董仲舒自己的解释,是人体察天意而取“仁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19。人之“取仁于天”,亦即“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为仁”20,是按“天志”变化血气的结果。在董仲舒看来,人以“天志”变化血气,亦即“仁造人”21,意味着人呼应“天志”以“仁”为人的本质。“仁”作为人的本质,按照董仲舒自己所说:“仁之为言人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22;“仁者所以爱人类也”23,“仁”作为人的本质,不是从人爱自己的意义上强调的,而是从人爱别人的意义上强调的,董仲舒强调:人的本质不是体现在个体自爱,而是体现在群体他爱。人不可能不“爱我”,或者说人根本做不到不“爱我”只“爱人”,所以尽管董仲舒将人之“仁”规定为“爱人”,但他仍然要就人“爱我”与“爱人”的关系来谈“仁”的本义。董仲舒所谓“爱人”,是指“泛爱群生”24,那么他以为如何才能由“爱我”过渡到“泛爱群生”呢?董仲舒似乎也认为要完成此过渡,除“推恩”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推恩”,董仲舒没有作更多的阐释或说明,他在使用这个范畴时,只说了一句:“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25,但这一句,却使孟子的“推恩”说法加深了哲学内涵,因为它点明了“推恩”分内外或曰体用的道理所在:就客体而言,推恩是人之个体的内在本心外在化为对人的泛爱,由个体“为仁”到对群体的泛爱,意味着人26之生命精神取向在价值上有别:推恩是将“爱我”之心推广为泛爱之心,其所以“大”,是因为这一爱心之推广在时空上是广远的,无任何局限,具有普遍性;而就主体来说,“推恩”意味着主体自觉地“为仁”,其所以“美”,是因为这一道德体认属于自然而然地呈现,具有无所为性质。《孟子·告子下》云:“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27,认为人的生命之美好在于其充实,而充实的生命一旦外在客观地光辉起来,生命就是伟大的。由此看来,董仲舒所以借用孟子“美”与“大”词语从价值层面区分“推恩”之内在与外在、主体与客体之别,想必也是因为他有着与孟子一样的生命情怀。
如果说汉代“仁学”的特色在于将孔孟“仁学”由“人学”变为“神学”,那么宋明“仁学”之特色则在于将汉代神学化的“仁学”解构为哲学化的“仁学”。宋明儒家对汉代神学化“仁学”之解构,一方面恢复孔孟“仁学”之“人学”性质,另一方面扩展孔孟“仁”范畴内涵,将孔孟用以规定人之本质的血亲情感或曰亲情形而上化,提升为人的道德本体。宋明“仁学”对孔孟“人学”的恢复,不是简单地否定汉儒之“仁者天地之心”而重提孔孟之“仁者人也”,而是将人的生命与天地万物的“生生之德”作一体把握,以人的生命精神体悟世界万物之“生意”,以人的道德本体为世界万物本体。周敦颐的《通书》有云:“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28,将“仁”界定为“生”。这个定义,意义重大,因为整个宋明仁学之所谓“仁”,在理念上都未突破这个定义,例如朱熹在论“仁之体”时,也是以“生”界定“仁”:“天地之心,只是个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叶条干,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穷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干枯杀了,这个是统论一个仁之体”29。王阳明同样强调“仁”乃“生之理”:“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30
这一由“生”所确定的“仁之体”,从二程到杨时再到王阳明,都异口同声地称之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一体之仁”是说由于仁这个本体,世界万物才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张载讲“民胞物与”,强调民众都是我的同胞,万物皆为我的朋友。比他稍后的理学家解释说:这个说法,就是在讲“仁者以万物为一体”31。
“仁者以万物为一体”,相比于《中庸》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32、《孟子》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33,其对儒家“仁学”的发展,已非简单地体现在“推己及人”与“仁民爱物”,也不简单体现在强调由血亲之爱走向爱别人再由爱人走向爱物,而是体现在它确立了这样的仁学主旨:仁是哲学范畴之客体与主体所共同具有的本质,在仁的范畴里,万物与人类是本体一样的存在。宋元明清理学家将这一本体命名为“天理”,而其所谓“天理”,就是将“仁”这一人之根本的伦理34抽象为超绝的本体。朱熹说:“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35;王阳明说:“良知即是天理”36,虽说法各异,但都强调“天理”与“仁”密不可分。
在理学家的解释里,“仁”作为超越本体,其普遍意义的实现,在途径与方法上,也只有靠“推恩”,别无他途。其中道理,朱熹解释得很明白:“不能推恩,则众叛亲离,故无以保妻子。盖骨肉之亲,本同一气,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其余,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自易以及难”37。朱熹指出了“推恩”对实践仁、落实仁、实现仁的必要性:人不可能因类相同而本分地去爱民爱物,人要实现普遍的爱心,就必须由骨肉血亲之爱由近及远一步一步地往外推广扩充爱心,最终实现万物一体之仁。
三、“仁爱”比“兼爱”“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
一种学说或一种系统理论是否有价值,固然要看它对人类文明之构成是否做出了贡献,更要看它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这两种说法,看似难以区分,实则很容易分辨。就前者而言,大凡名曰学说或曰系统理论的人之思想创造,莫不对人类文明之构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不能因此就断言:人之创造的所有学说或曰系统理论,对人类文明之构成,都做出了程度相等的重要贡献。不同的学说或系统理论对人类文明构成的贡献,其实有大有小。要分辨其大小,只能通过比较。儒学对人类文明之贡献究竟有多大,同样需要通过比较来揭示。这一比较,就中国文化自身比较而言,应将儒家“仁爱”说与墨家“兼爱”说相比较;就中外文化比较而言,应将儒家“仁爱”说与基督教“博爱”说相比较。通过这两方面的比较,儒家文明的特色,就会自然呈现出来,用不着再去费力论证。
先比较儒家“仁爱”说与墨家“兼爱”。儒家“仁爱”说与墨家“兼爱”说无疑有相通之处。其相通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两者都主张“泛爱众”38,反对将对人的爱限定在特定的人群或阶层,强调“爱人”对于人类存在的普遍价值;二是两者都主张人与人要相处以“爱”,反对人际关系上的冷酷无情。但与儒家将这两点主张建立在“性善”论理论基础之上不同,墨家主张这两点在理论上依据的是功利论。从墨子开始,墨家一直将“兼相爱”与“交相利”并提,强调人与人之所以能相互关爱是因为人与人能互利。墨子说:“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成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君说之,则士众能为之。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此何难之有”(《墨子·兼爱中》)。人与人不分亲疏的“兼相爱”取决于人与人能互利,而人能做到互利就因为人本来是可以互利互爱的共同体,只要你给别人以爱、给别人以好处,别人必然反过来予你以爱、予你以好处。墨子未进一步说明这一反向回报行为所以产生的人性论缘由,他关于“兼相爱、交相利”反反复复的论述,只是一再强调人与人不分亲疏的“兼相爱”是基于人之“交相利”的功利取向所做出的必然抉择。这一抉择表明,墨家所提倡的“兼爱”非抽象的泛爱,而是以“利益交换”为根本准则来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互爱。“互爱”既以“互利”来维系,则人与人之所以有必要相互关爱,当然是因为“兼爱”会给人带来“互利”,这就好比价值对等的物与物之交换对交换双方都有利一样的道理。
对墨家将人所以能“互爱”归因于人能“互利”之“兼爱”说,儒家深深不以为然,因为儒家认为人若以“利”为原则来交往,非但不能导致相爱,反倒必然造成相残。个中道理,孟子说很明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也,千取百也,不为不多也。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孟子规劝梁惠王的一番话,就一般含义而言,假如人人都循自己的利益优先原则去谋利,这在可取的利益毕竟有限的前提下,就只能以损害别人的利益来争得一己利益的最大化;人人都想争得最大化的利益,除了走向相互残害,决不会有另外的后果。正因为以“互利”维系“互爱”,在孟子看来,是不可靠的、不可能,更是危险的,所以他尖锐地批评墨家提倡“兼爱”是“无父”。这个批评,一般的解释是说:孟子以为“兼爱”会导致爱别人的父亲与爱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差别,则各个人的父亲对各个人来说,就失去了作为各个人父亲的特殊意义,于是各个人有父亲就如同无父亲。但是,这样理解尚在表面,深入琢磨,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假如人之“互爱”由“互利”来维系,则人之是否爱“父”,就取决于能否因此得“利”,一旦无“利”可得,人就不会爱“父”。人于“利”贪得无厌,则一旦主张爱父须得“利”,势必导致不爱父。有父不去爱,岂不等于无父。
王阳明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以利益原则维系的人之互爱为何不能视同仁爱。在与弟子讨论墨家“兼爱”何以不能称为“仁”时,他公开了自己的思考所得。弟子问他:“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阳明回答道:“此亦甚难言,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39。阳明的这一回答,乍一看,好像所答非所问,但细想想不难明白:阳明是以“仁爱”是什么反衬“兼爱”不是什么。在阳明看来,墨家的“兼爱”尽管也提倡“博爱”,但毕竟不能与儒家的“仁者爱人”并提,因为儒家仁爱以孝弟为本,爱人的情感是内在“仁理”的自然呈现,而“兼相爱”则主张将别人家的父子兄弟与自家的父子兄弟一样爱戴,其爱缺乏内在(人心)“生意”之坚实的情感基础,其爱的情感只为外在的利益原则所支配。因为不是发端于内在,而是取决于外在,所以“兼爱”没有根本保证,随“利”之有无变动而变动,不具有仁爱那般稳固不变的特性。
墨家之“兼爱”,人与人之交往,可谓“交以利”;而儒家之“仁爱”,人与人的交往,则可谓“交以义”。所谓“交以义”,就是主张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始终贯彻道德理性,以“爱人”为根本原则。对儒学来说,“爱人者人恒爱之”40,人们一旦以“爱人”为原则来交往,爱人者也会为他所爱的人永久地关爱。孟子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与墨子所谓“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从文字表面,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含义,但如果从“仁爱”不同于“兼爱”的立意来谈,就会认识到其差别。孟子那样说,强调的是:人一旦关爱别人,就会造成被别人永久关爱的结果;而墨子那样说,强调的则是:人只有先主动关爱别人,才能造成别人也相应地关爱他的结果。这一浅层差别其实反映了这样的深层差别:墨家以为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计较而被动地关爱他人,儒家以为人本乎自己的善良本性而主动关爱他人。虽然都主张要关爱他人,但关爱他人的情怀迥异:墨家“兼爱”持个体利益优先情怀,儒家仁爱则持群体利益优先情怀。与各自的情怀相一致,墨家思考集中在如何避害兴利,儒家思考集中在如何实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归根到底,“兼爱”与“仁爱”的不同,是两种人生境界的不同。如果说人生不是“苦”而是“乐”的话,墨家“兼爱”所谋求的是人之一己之“独乐”,而儒家“仁爱”所谋求的则是群体之“众乐”。孟子说“众乐乐”贵于“独乐乐”、(《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孟(子)范(仲淹)前后相隔千余年,他们关于人生之乐乐在“爱人”41的生命精神体悟,典型地反映了儒学的人生价值观。而儒家的这种以群体“众乐”贵于个体的“独乐”、以群体的“众乐”先于个体的“独乐”的大爱精神——以“众乐”为“乐”,正是儒家体悟出人生不是“苦”,而是“乐”之关键所在。
再比较儒家“仁爱”说与基督教“博爱”。韩愈于《原道》中界定“仁”云“博爱之谓仁”42,这让人很容易将儒家的“仁爱”与基督教的“博爱”相提并论,但细致地分析的话,就会明白:儒家的“仁爱”与基督教的“博爱”,仅在抽象地提倡“泛爱众”这一点上可以相提并论,而在本质上并不能混为一谈。
基督教的“博爱”,就《马太福音》来说,有两个根本原则,一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上帝,二是爱人如己。这两个原则,被规定为基督教“最大的诫命”,成为基督教法律与教理的总纲:“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法律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法律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法律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43。为这两条诫命所限,基督教之“博爱”无论作何种广度与深度的解释,都不可能超出以下内涵:人首先要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上帝就要无条件地服从上帝,而人所以能普遍地施爱予他人,是因为人听从了上帝你要“爱人”的召唤:人当像关爱自身一样关爱他人。由此可以看出,基督教“博爱”的根本原则,与儒家“仁爱”根本原则,是相异的、冲突的,因为儒家的“仁爱”不讲对上帝的爱,只讲对人的爱;而且儒家强调爱人首先爱的是自己的父母,其次是自家的兄弟姐妹,然后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情感比附的方式,实现对他人普遍的爱。儒家所强调的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的爱他人,与基督教所强调的像爱自己一样的爱他人,虽然都以“爱他人”为归宿,但爱之情怀各异:儒家重家庭情感,基督教“博爱”重个人情感。为个人情感所左右的“博爱”与为家庭情感所左右的“仁爱”,在“爱”之情感发泄机制上,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取决于血缘亲情认同,后者取决于个体人格关切。在深层里,这一区别,其实反映了立“公”还是立“私”的对立,儒家“仁爱”讲的是出于“公心”的爱他人,基督教“博爱”讲的是出于“私心”爱他人;前者虽然讲“爱有差等”,但因为出于“公心”,以家庭的利益与命运关切为关切,反倒客观上更能广泛地爱他人,实现“泛爱众”;后者虽然不讲“爱有差等”,甚至标榜平等地爱一切人,但由于出于“私心”,以个人的人格与前途关切为关切,反倒客观上难以实现“博爱”,即不能真正做到爱己与爱人毫无差别、爱别人如爱自己。
“爱人”行为的成立,对儒家“仁爱”来说,是亲情之爱的扩充;对基督教“博爱”来说,是自我之爱的扩大。儒家的亲情之爱,最为看重的是父子之爱,而基督教并不看重人间的父子之爱,因为基督教教理规定:人人皆上帝之子,爱上帝才是人第一位的本分,人间的父子之爱决不能也不该超越人对“天父”(上帝)的爱。在人皆上帝之子这一教义的限定下,基督教之“爱人如己”,实际上取消了人间父子之爱,将父子之爱等同于兄弟之爱。儒家重视父子之爱,基督教将父子之爱等同于兄弟之爱,其差异决定了“仁爱”与“博爱”在价值认同上的差别:兄弟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基督教“博爱”标榜人之首要价值是自由;父子的地位实际不平等,所以儒家的“仁爱”强调人的首要价值是孝。以个人自由维系的“博爱”与以家庭“孝道”维系的“仁爱”,其实体现了中西文明不同的价值认同:中国文明重家庭,西方文明重个人。
家庭是命运共同体,相对家庭,个人只是构成该共同体的一分子。依儒家“仁爱”理论,由各个个人构成的家庭命运共同体,是靠血缘亲情维系的,不讲血缘亲情就等于破坏、分裂家庭命运共同体。所以儒家“仁爱”强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44,将“亲亲”规定为“爱人”的最高价值。基督教“博爱”则不然,它可谓一己为大,并不将尊双亲看作最高价值。既然一己为大,不希望为亲情所束缚,那么基督教所谓“爱人如己”又如何能实现呢?基督教所谓“博爱”又如何实现呢?依基督教教义,人可以靠契约精神维系“博爱”,实现“爱人如己”。这也可以说,在基督徒看来,人之爱人,不是自己付出无私的情感,而是出于守约,即履行自己与神(上帝)的契约。人与上帝的契约是无形的,它其实只意味着人单方面心甘情愿地履行信仰承诺,坚信人只有信守对上帝的承诺,才会实际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进入天堂,这就是基督徒爱人所得到的回报。求回报,符合契约精神,却有违儒家“道义”精神,因为儒家“道义”只讲奉献而不讲回报;求回报,是功利主义的考量,这对儒家“道义”考虑来说,是不足取的,因为儒家“道义”坚持“正其谊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见,儒家“仁爱”与基督教“博爱”,虽然都倡导人之个体对他人的奉献,但两者在奉献之动机上的差异不言而喻:儒家否认“爱人”以求回报的合理性,提倡不杂私念之纯道德的泛爱;基督教则肯定“爱人”以求回报的合理性,强调只有博爱方能中选(由潜在的上帝选民转为被上帝实际选了的选民)之回报。儒家“仁爱”与基督教“博爱”之不同,就动因而论,就在于“仁爱”是无动机的纯道德的倡导普遍的爱,而“博爱”则是有动机的功利性的倡导普遍的爱。两者都倡导普遍的爱,足以证明儒家“仁爱”与基督教“博爱”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但仁爱提倡无动机付出爱心而博爱主张有动机付出爱心,又足以证明两者在所以爱人的精神境界上导向不同。
儒家“仁爱”精神境界之不同于基督教“博爱”精神境界,是从道德理性高于功利理性、道德文明高于物质文明的意义上说的;而所以这样说,并不是为了以“仁爱”的道德理性否定“博爱”的功利理性,更不是以“仁爱”文明否定“博爱”文明,而是为了从精神境界上区分“仁爱”与“博爱”之人生导向上的不同意义:“仁爱”的人生导向,更贴近人之本性,因而对人生指导意义比较实际;“博爱”的人生导向,其实有违人的本性,因而对于人生的指导意义比较理想。比方说,基督教主张:人家打你的左脸,你再伸出右脸让人打,而儒家则强调: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两种主张,前者提倡屈己以爱他人,后者提倡率性待人,爱可爱之人,恶当恶之人;前者所以屈己以爱,显然是因为坚守与上帝的契约,以人人是平等的兄弟的信念化解委屈与烦恼;后者所以顺从自己的本性爱人、恶人,显然是因为将人之存在归结为人性,以为屈己顺人有违做人的本质。仁爱不提倡屈己以爱人,博爱提倡屈己以爱人,就每个个体觉悟自己的存在意义来说,在精神境界上,前者异于后者是不言而喻的。基督教的“博爱”是契约精神的高度体现,而儒家的“仁爱”则是人本精神的高度体现。契约精神以人为手段,追求的是人之利益上的平等;而人本精神则以人为目的,追求的是人之存在意义上的平等,两者在精神境界上的不同,也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1 这并非排斥从文化类型之差异上分析不同文明之相异的特性,只是强调这样一个认识:文明之比较,重在抉发不同文明在价值与意义上的差异,未必要走向文化类型之同异比较。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8页。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页。
4此系赵岐对孟子有关思想的概括,参见姚永概:《孟子讲义》,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92页。
5唐君毅对此说有详细的论述,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21页。
6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云云,即包含此意。
7即返归“不忍人之心”,面对别人的不幸、痛苦甚至悲惨,自然地呈现其同情、怜悯的情感。
8具体讲,即推理能力。用孟子自己的话说,叫做人能“充类”。
9《论语·里仁》第15章有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10此非孔子原话,是本文作者根据自己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理解所做出的概括。
11爱无差等,即对亲人之外的人付出一样的爱。
1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98页。
1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3页。
1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4页。
1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6页。
1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6-357页。
1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1页。
1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9页。
1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9页。
20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18页。
2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5页。
2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9-250页。
2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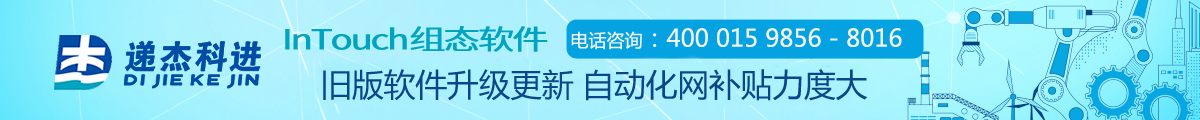

评论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