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DongHua”人文观察:自动化行政决策】
类似地,自动化行政决策所面临的算法黑箱、算法可理解性等问题,也可以通过对“算法”的法律规制而加以解决。数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可以在系统论的“协同演进”(coordinated evolution)路径上得到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是数治对法治的改写或重构,而应通过法治工具系统与数治技术的协同演进,不断发展和改进“数字化法治系统”。
王锡锌:法治政府建设的“数治”与“法治”|自动化行政决策所面临的问题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外法学》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宪法与行政法、政府规制、数据治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催生了“数字化时代”。在此背景下,政府通过对个人和组织的数据采集、处理及应用,不断增强其“数据权力”。这种“数据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深度融合,促成了“数治”。在本质上,数治是政府通过技术赋能而进行的治理手段升级,其内核仍然是公共权力的行使。在法治主义框架中,公共权力的行使应当纳入法律控制系统。无论是从法治逻辑还是法治实践看,数治都需要受到法治的约束。
在当代公共治理背景中,数治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为公共安全目的而进行的监控、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目标的信用监管、对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管控所引入的“审慎监管”、预防性监管、疫情防控中广泛采用的“码治理”,都是数治的典型表现形式。这些应用场景也表明,数治实际上是运用数据分析、画像、决策等技术而促进行政权能有效实现的一种新的治理技术。
在规范层面,这种新的公共治理技术应当融入法治系统;但在技术层面,数治与法治存在明显的张力。概括而言,这种张力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法治以自然语言为规则表达;数治以代码、算法等人工语言为规则表达。第二,法治强调以事先明确的规则为指引;数治以可得的数据分析和处理为行为指引。第三,法治以公开、参与、可理解的程序规则对行为进行理性化制约;数治以内部的、机器计算作为行为的理据,因而面临“算法黑箱”难题。第四,法治强调对权力主体的“可归责性”;数治则导致权力主体的归责逻辑发生变化。第五,法治强调以法官和司法系统为代表的审查和纠纷解决;数治则依赖专业技术人员对技术性问题的判断评价。数治与法治之间的这些紧张关系,在当下的“数字化法治政府”建设中如何缓解,是一个重大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数字化法治政府是“数治”与“法治”的结合。前者是将信息技术和数据技术作为“政府赋能”的工具,主要关注治理的技术手段和工具价值;后者是对政府的行政权力行使设定的规范和价值框架,目的在于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约束和理性化规范,因此既是工具系统,也是价值系统。
事实上,数治与法治是两个可兼容治理系统。数治主要是一个治理技术系统,而法治则是工具和价值的二元复合系统。但二者也存在技术与价值、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紧张关系。数治对法治的冲击,主要表现为前者对法治系统中的“工具系统”的冲击。作为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权责制度、程序参与、理性、公开制度、行政问责制度,在数治背景中将遭受来自数字化技术的冲击;数治作为治理技术具有“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特性。数治的这些特性容易与法治产生冲突。但数治对法治的冲击,不会也不应该颠覆法治的“价值系统”。在数字化时代,法治系统中对权力运行公开、公正、理性行使,对个体权利保障、对权力的约束等价值,仍然应当得到坚守。这意味着,面对数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应当对法治的工具系统进行相应的“工具改造”,并通过法治系统中的工具改造实现数字化时代的法治价值功能。例如,数治需要数据驱动;相应地,可以通过法治方式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共享、应用、责任、救济等环节进行规范,将其纳入法治框架。类似地,自动化行政决策所面临的算法黑箱、算法可理解性等问题,也可以通过对“算法”的法律规制而加以解决。数治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可以在系统论的“协同演进”(coordinated evolution)路径上得到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是数治对法治的改写或重构,而应通过法治工具系统与数治技术的协同演进,不断发展和改进“数字化法治系统”。事实上,在数治技术应用广度及深度不断增长的当代社会中,一方面应当坚守法治的价值系统,另一方面也应当拥抱数治技术并相应地改进法治的工具系统。当前,我国法治研究和实践中提出并不断展开的数字法治、数字法学、数字化法治政府等概念,都可以在数治—法治的分析框架中得到规范性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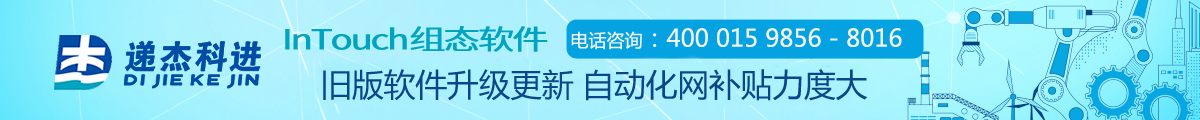

评论排行